网上有关“饮食对人类的发展有何意义?”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饮食对人类的发展有何意义?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食物与进化的关系──素食是人类未来进化的必由之路
有时候,一些在科学界尚未形成定论的推断会在公众中被当作真理流传。“肉食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论断就是其中一例。本论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告诉大家这其实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推断,没有严谨的科学依据。本文作者侯亚梅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在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规格发表文章驳斥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东亚的直立人比非洲直立人缺少智慧和适应能力,并引起国际轰动,促使考古研究不得不对亚洲人类文明起源进行重新评估,2004年她曾获得国家“首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称号。胡宏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而2009年11月则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达尔文不仅在自然科学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博爱与睿智也极大的影响了人文科学。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科学家对科学、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的影响能与达尔文相比。达尔文的爱心包含了所有的动物。他说:“人与高等哺乳类动物在智力方面没有根本的差异…在精神方面人与高等动物之间有很大差异,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量的差异,不是本质或类上的差异 (1)”。他明确的告诉我们:“对所有生物的爱是人类最高贵的品德 (2)。” 民以食为天,在人类进化史中饮食对人类的生存无疑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出于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与爱,达尔文本人是一位素食者。不过许多营养学家在饮食观点方面并不认同达尔文的观点,他们试图通过史前考古从生命进化中发现一些为自己的肉食营养学观点提供证据的事实。如美国卡萝琳·M·庞德博士在其所著的《生命与脂肪》一书中指出“转向食肉的时间正好与人科动物化石的颅腔迅速大的时间相吻合。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这种相互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食肉直接导致了智力的改善,从而为进化成为现代人铺平了道路。所以,从史前到现在,肉食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一直是一种比较宝贵的食物。”使人体获得完全蛋白、维生素以及其它各种营养物质的来源。特别是肉类能提供锌、维生素B12、钙、铁和维生素A等基本营养素,而这些营养物质很难在素食中摄取”。 依据卡萝琳·M·庞德博士的观点,素食者会令人营养不良,而且还会使人的进化停止,智力减退。这段耸人听闻的说法会使任何一个准备尝试成为素食者的人望而却步,而一个喜欢吃肉的人看了这段话就更会坚信素食者是自虐狂,反而更加相信吃肉有助于人类的进化。然而,如果作较为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并没有科学的依据。下面我们来作一些详细的分析。 生命的进化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事件,科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已经可以给出一个大致的生物进化框图,然而依据这些有限的事实得出结论时仍需非常谨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其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把科学的这种特性称为可证伪性。他说:“应该作为分解标准(指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言之,我不要求一个科学体系能一劳永逸地在肯定的意义上被选拔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被选拔出来: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能被经验反驳。”正因为如此,科学研究中常有不同的观点在相互争论,要搞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需要对各种观点做辩证的分析,进行深入探究后才能获得较为正确的结论。本文试图通过对食物与进化关系的分析,为人类进一步迈向更高等的生命进化提出一些饮食方面的建议。 好的科学研究离不开人文的精神指导,在研究人的进化问题时,如果离开了道德的指导极易得出荒唐的结论。为了得出更为客观正确的结论。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与此有关的各种观点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分析,看科学关于肉食与进化之间关系的结论到底如何。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有关人类进化方面一些公认的事实。 依据人类学的研究,人类进化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以下文字中的人类学资料来源于雅·雅·罗金斯基, 马·格·列义著的《人类学》:人的前驱(南方古猿)时代,南方古猿从其树栖的祖先那里得到的重要遗传特征是能够使用物体的手以及大脑皮层的相应部分。在生活习性上,南方古猿从其祖先那里获得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群居性。南方古猿首先应该具有了作为用手动物和群居动物所具有的那些能力,它们具有寻找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但还不具备有意识地制造工具的能力。由于年代久远,南方古猿详细的食物结构很难从田野考古挖掘事实进行推断,我们只能粗略地推断南方古猿可能是杂食动物。不过依据美国人乔治·萨勒研究在自然条件下山地大猩猩的生活和行为的著作以及英国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坦噶尼客湖东岸对黑猩猩的研究著作,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关于猩猩饮食方面的详细资料,以弥补考古学的不足。依据这些现代动物学家的观察,在179个山地大猩猩的巢约有半数在地上,而黑猩猩的巢则通常建在树上;大猩猩是和平的动物,而黑猩猩则往往具有攻击性;大猩猩完全以植物为食(它食用约29种食物),而黑猩猩则经常食肉,它捕食的对象有疣猴、小狒狒、红尾猴和兰色的长尾猴等;大猩猩、黑猩猩与南方古猿有什么关系?
直立人,即远古时代。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能有意识地制造工具,远古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手斧。考古学家认为舍利时代的手斧的主要用处是发挥最符合其形状与重量的功能,既用于砍砸与粗削;这些作用有两个目的:(1)制造原始的棍棒与带尖的木头工具,比如木矛等;(2)用于分解已经打死的动物的尸体以及敲开动物的头骨取髓等。所以直立人也是杂食动物。直立人的脑量比猩猩的脑量大幅增加(从435-650立方厘米增加到800-1225立方厘米)。美国卡萝琳·M·庞德博士在其所著的《生命与脂肪》一书中所采用的“转向食肉的时间正好与人科动物化石的颅腔迅速增大的时间相吻合”观点可能就是基于关于直立人制作工具手斧等的功用提出的。
尼安德特人,或古人时代。对于古人文化,我们可以根据大量的莫斯特遗址的出土的工具作出判断,莫斯特工具的特点是加工更为精细、规整,形状更为多样。出现了简单的骨制品。根据在莫斯特遗址广泛分布的篝火、烧骨、灰烬堆的遗址看来,完全可以推断尼安德特人已经具有人工取火用火的能力。所以从尼安德特人时代起,人类开始熟食,尼安德特人也是杂食动物。尼安德特人的大脑比直立人不仅脑量更大而且结构也有较大变化,比如颅内模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主要是在顶骨部位)增大等。有人以此推断熟食对大脑进化的重要性。
现代人或新人时代就不必多说了。 上述考古学家依据远古人类(或直立人)制作的手斧的石器的功用推断远古人类是吃肉的,这个结论或许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进一步推断吃肉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条件那就有问题了。营养是否全面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可以看一看《不吃肉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吗?》一文。从文中可以看出素食不仅不比肉食营养差,而且比肉食营养好。如果再加上植物性中草药的调理,素食的营养远超肉类。有关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看专业书《素食者膳食指南》
综上所述,生命进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也是最复杂的事件,促使进化的因素众多,有多种理论解释进化机理。“食肉的假设理论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种理论,由于肉食动物比素食动物更为凶残好斗,容易导引出人类的进化是越来越多的依靠用来杀害的武器来获取肉食,一种史前的武器竞赛促进了脑的发展的结论,故很少有人认同该理论”。
食物与人类 #7 :农业的诅咒
辉格
2018
年7月27日
上一篇我讲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游动性降低,这三个轮番相互强化的因素,推动人类食谱沿质量光谱向下移动,这一过程在冰期过后气温回暖之际骤然加速,而在整个农业时代,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而且随着土地开垦和作物单一化,渔猎和畜牧成分萎缩,食谱在下移之后进而向下收窄,对谷物的依赖日益强化。
只有在某些大瘟疫过后的恢复期中,食谱质量才有所反弹,然后到哥伦布大交换(伴随着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瘟疫)之后在新世界大幅反弹,最后,直到工业革命和人口转型之后,才在中等以上收入地区出现全面反弹。
食谱下移和向下收窄对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不乏有人将导致定居农业的新石器革命视为人类遭受的一次诅咒,从饮食与健康角度看,确实如此,对于那些缺乏畜牧和渔猎成分的纯谷物种植群体,这一点尤为真确。
从进化角度看,谷物是特别可疑的一类食物,因为我们的旧石器祖先从未将它们当作重要食物来源,这意味着,如果它们有什么害处,我们的生理系统作出适应性改变的机会极为有限,因为留给进化适应的时间只有几千最多一万年,而事实上,谷物成为主食对健康所带来的损害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清晰展示。
龋齿
龋齿是特别典型的农业病,狩猎采集者中很少见;高碳水饮食为细菌创造了良好的口腔环境,典型采猎者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贡献的能量只有1/3,高纬度地区更低,而在密集农耕者中则高达2/3到4/5,而且农耕者对淀粉类食物的加工与烹饪更充分,甚至精制成饴(即麦芽糖,一种双糖),因而更容易被口腔细菌所利用,而采猎者能吃到的唯一“精制糖”是蜂蜜,可是蜂蜜本身含有抗菌成分。
这里我想顺便强调一下,我的读者中大概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蒙古或高加索人种,这两个人种在更新世末期都曾长期生活在接近冰川线或冻原的寒冷地带,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习惯,当我在『最近三四万年』这一时间情境下使用『我们祖先』这个短语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而对于他们,食谱中脂肪含量会比典型现代采猎者高得多,碳水则低得多。
所以考古记录中向谷物的转变总是与龋齿高发联系在一起,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稻米,东南亚稻米种植的出现似乎与龋齿没有确切关系,原因未明。
贫血
贫血在农耕者中很普遍,有些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则是缺铁,谷物不仅本身含铁量低,而且富含植酸(phytic acid),植酸会妨碍肠道对矿物质的吸收,因而提高缺铁缺钙缺锌的风险,所以植酸被营养学家归为反营养素(antinutrients),它在谷物麸皮中含量尤高(有意思的是,全谷食物眼下正广受推崇)。
贫血会迫使身体增加造血骨髓的量,因而在一些骨骼中(特别是颅骨的眼窝上穹处)额外形成大量蜂窝状空腔来容纳红骨髓,于是便留下了化石证据。
目前,全球仍有15亿人处于程度不等的缺铁性贫血状态,其中多数为营养不良所致。
发育不良
和采猎者相比,农耕者骨密度较低,因而骨骼强度较弱,可能是因为缺钙;但更能全面反映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指标是身高,因为身高与整个发育期中诸多营养与卫生条件有关,只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时,遗传基础所给定的身高潜力才能达到。
现代采猎者的身高普遍不高,与传统农耕者不相上下,但需要记住的是,自从农业起源以来,绝大部分生态位都已被农牧者占据,采猎者面对农牧民的扩张排挤毫无抵御能力(因为他们的群体太小也太缺乏组织),所以现存采猎者占据的都是边缘生态位,处境逼仄,如我在第五篇里所介绍,卡拉哈里昆桑人的营养状况极差。
但旧石器时代的采猎者并非如此,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末次冰期中生活于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平均身高1.79米,其中末次盛冰期的格拉维特人超过1.80米,然而经历了光谱革命之后的欧洲人平均身高降至1.66米,农业时代再降至1.65米,这其中当然可能有气温变化的影响(寒冷地区的动物倾向于大体型),以及新石器革命后历次移民造成的遗传成分改变,但主要不是,有两个证据:首先,在近代营养状况反弹之后,多数欧洲国家身高都回升至了1.80米以上,其中荷兰最突出,从19世纪中期的1.65米升至1990年代的1.84米,其次,农业时代身高下降的趋势在东欧表现的更缓和,平均身高始终维持在1.70以上,而我们知道,东欧的农业密集化程度长期落后于西欧,气候与土壤条件也让他们保留了更多畜牧成分,这些证据表明,欧洲人基因组给定的潜在身高就是1.80米以上。
来自其他地区的考古记录也显示了同样趋势,中国和日本的稻米种植者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初几千年里平均身高下降了8厘米,中美洲的玉米种植者,男性身高下降5.5厘米,女性8厘米;两个事实清楚的揭示了传统农耕者的身高被营养条件所压制:任何农业穷国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平均身高都大幅提高,任何从农业穷国向富裕国家的移民从第二代开始身高都大幅提高。
关节损伤
化石证据显示的另一个健康问题是,农耕者的关节损伤率普遍比采猎者高,包括骨性关节炎,这既是因为营养不良,也是因为农耕者劳动负担更重,劳动时间更长,正如我在上一篇里所讲,食谱下移本身就是马尔萨斯型创新的后果,此类创新让人类能够以不断加大的劳动投入从给定资源中榨出更多一滴营养。
而且农业劳动(包括农业生活特有的那些家务)所涉及的身体姿态,肢体动作和负荷分布,都与狩猎采集活动大异其趣,而我们的身体是为后者而塑造的,所以,即便劳动强度相当,农活也更不益于健康,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与农活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体育或健身项目(我能想到的只有举重与拔河),却能在众多项目中发现狩猎和捕鱼的影子。
大脑
人类大脑的体积在过去两万多年里缩小了10%,对此有许多种猜测,尚无定论,有人认为DHA(一种在神经发育中起重要作用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缺乏在其中起了作用,脂肪曾占人类食物的1/3,密集农业却将它降到了10%甚至更低;DHA虽然可以在体内合成,但所需材料EPA也是一种脂肪酸,而且体内合成效率可能跟不上大脑发育高峰期的需求。
这是一种供方解释,可能需要与某种需方解释搭配才能成立,因为大脑体积并未像身高那样在近代营养改善后普遍反弹,所以看起来并非单纯被营养条件所压制,或许,出于某些原因(比如体型缩小,肌肉量减少,温顺化,分工细化,神经元密度提高或布线合理化……),我们不再那么需要这么大的大脑了,而同时营养匮乏(特别是DHA匮乏)使得供养这颗高能耗大脑的负担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于是基因组便作出了向下调整的反应。
麸质过敏
麦类谷物(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所特有的麸质蛋白(gluten)引发了众多健康问题(至少在对它敏感的人群中),包括乳糜泻,非腹泻性麸质过敏,平衡机能失调,和过敏性皮疹或溃疡,尽管没有留下化石证据,但这些症状与谷物和农业的关系如此直接以至无需考古证据即可确定。
由麸质蛋白引起的问题虽然表现多样,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机制:免疫系统对这种陌生蛋白作出了过度反应,这不难理解,从进化史的尺度看,麦类谷物对人类确实很陌生。
麸质问题究竟有多普遍,眼下还不得而知,虽然目前的流行病学统计中被识别为麸质过敏的人口比例不到10%,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麸质过敏症状多样因而诊断不容易,其次,麸质问题最近才开始被医学界关注,所以患者和医生还很少朝这个方向考虑问题,第三,从政治上看,你很难指望农业大国(比如美国)的政府会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而政府拨款在当今医学与营养研究的预算中占了绝大部分。
传染病
定居恶化了卫生状况,定居点积累的垃圾和囤积的食物养活了大量老鼠、蟑螂和苍蝇等人类伴生动物,也为诸多病菌提供了温床,还会污染附近的水源,定居者无法像游动采猎者那样可以通过不断搬迁营地而摆脱它们,同时,人畜共生的环境也大幅增加了有害微生物的种类,比如导致肺结核、流感、天花和麻疹的那些。
更重要的是,定居农业将人口密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并且通过商人,流动性工匠,流浪艺人和乞丐,军队,行政官吏,在庞大人群中形成经常性人口流动,而集市与城镇又为这张流动网络提供了中心集散节点,这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创造了极佳条件,特别是那些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在稀疏分布的小群体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病原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宿主群体消灭殆尽,于是自己也失去了存身之所。
诚然,大规模定居群体因为长期接触各种病原体,其免疫系统积累的武器储备更为丰富,因而更可能在各种瘟疫中幸存下来,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免疫系统与病原体的长期搏斗不仅消耗能量,也会抑制其他生理机能的工作,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当遭遇饥荒而营养状况恶化时,这个持续高负荷工作的系统可能全线崩溃,所以瘟疫往往紧随饥荒而来。
蛋白匮乏
食谱向下收窄,对主粮的依赖日益加重,也带来了严重的营养均衡问题,这一点在中低纬度的水稻和玉米种植区尤为严重,因为水稻生长期短,一年可种多季,因而供养人口密度高,在有了水田、灌溉和梯田技术之后,几乎排挤了所有其他粮食作物,中低纬度季风带的充沛降雨使得留给牲畜的土地极少,而玉米不仅高产,而且对土壤要求低,因而也很容易挤掉其他作物。
精制米的维生素B1含量极低,导致东南亚稻米区普遍流行脚气病,玉米的维生素B3和色氨酸含量太低,因而以玉米为主食者的美洲人多患糙皮病,然而,更普遍更严重的营养失衡是蛋白质匮乏,谷物的蛋白含量普遍较低,尽管以豆类为辅食可有所弥补,但与采猎者和畜牧者食谱中高比例的肉鱼奶相比,蛋白量仍差得远。
而且植物蛋白有很多问题,要么氨基酸不全,要么氨基酸组成比例不佳,要么吸收效果不好,要么有其他附带缺陷(比如过敏),营养学家用蛋白质质量(PDCAAS或DIAAS)和生物价值(biological value, BV)两个指标来衡量各种蛋白源的营养价值,前者度量蛋白源的氨基酸齐全性和搭配比例,后者度量吸收并用于机体结构(而非用作能量来源)的比率,两项测量中,得分最高的都是禽蛋,其次是奶制品,然后是肉类,植源蛋白得分普遍偏低,谷物尤其低,豆类稍高。
总体上看,植物蛋白的质量得分大概只有动物蛋白的一半,唯一质量得分与动物蛋白相当的植物是大豆(DIAAS=0.9,与牛肉接近,鸡蛋为满分1.0),但大豆的BV得分就只有74,还是植物蛋白里最高的,而鸡蛋、牛奶和牛肉的BV分别为100、91和80,其他豆类就差很多,谷物更差。
植物蛋白源中质量最高的大豆,古代只分布于东亚,直到近代才传播到其他大洲,而且它和其他种子类食物一样,富含植酸,也和其他豆类一样,嘌呤过高,容易导致痛风,而且其蛋白质也会让许多人过敏。
密集农耕造就的蛋白匮乏,迫使人们挖空心思的搜罗开发一切蛋白来源,鱼虾,青蛙,泥鳅,螺蛳,田鼠,黄鼠狼,麻雀,知了,蚱蜢,毛虫,蛾子……,当农耕者将土地开发殆尽,生态被全面改造之后,能找到的就只有这些小动物了,辛苦搜罗一年得到的蛋白量,还不如一头猪。
这些努力的最极端表现是吃人,食人俗的地理分布明显和蛋白匮乏有关,将食人俗推向极致的是美洲人,在中美洲玉米高产区,人肉成了系统性和经常性的肉食来源,玛雅和阿兹特克城邦常常在祭奠仪式上杀死成千上万的俘虏,用作人牲献祭,随后尸体被分给贵族和武士拿回家吃掉,俘虏被推上祭坛之前的等待期中会得到充足食物,以便催肥。
在阿兹特克,获取俘虏甚至成了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因而战术策略也向尽可能多抓俘虏倾斜,抓获俘虏的数量(而不是杀敌数量)成为考核战功的主要指标,这一倾向最清楚的体现在阿兹特克晚期的所谓荣冠战争(xochiyaoyotl)中,这是一种仪式性战争,和扩张领地,争夺霸权,压服对手等常见战争理由无关,双方约定日期和地点,派出相同数量战士,只能使用短兵器做近身搏斗,唯一的动机就是获取战俘。
蛋白匮乏在美洲如此严重,是因为他们缺乏肉畜,也没大豆,美洲人驯化的唯一大动物是羊驼,数量很少,主要用于取毛和驮运,中美洲农民驯养用来吃肉的动物只有豚鼠,每只豚鼠仅能提供小几百克肉食,但他们也珍之如宝。
文明之暗面
可能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时会提出疑问:既然定居、农业和谷物带来了这么多问题,如此恶化了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为何你在第五篇里还表现的那么欣快,将食物存储、食谱下拓、定居、农业,特别是谷物的开发,视为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甚至将谷物称为文明试金石,难道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要我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农业确实恶化了人类营养与健康,但我不会像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那样宣称“从事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我相信这只是他为强调上述事实而采用的一种修辞术,而并未从字面上当真,如若不然,他就大错特错了。
向农业的转变是一系列分散个体抉择在漫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后果,事后拉远镜头看,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但没有任何个体预见、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革命,因而根本谈不上谁犯了什么错误(此类评判只有当你把自己想象成引领全人类航向的伟大舵手时才有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个体抉择,完全可能都是理性的,并给当事个体带来了切实好处。
比如开发谷物,最初可能只是作为季节性补充,帮人熬过猎物低产期,当初这么做的人当然得到了好处,可是当这一做法流行开之后,其长期效果是拓宽了生态条件所施加的人口瓶颈,于是人口增加,摊掉了最初的好处,而同时食谱却下移了,但这是好多代人之后的情况,和最初开发谷物的人没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他们比没有这么做的人留下了更多后代,这算个错误吗?)
有人会接着问:就算没有人犯错,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呢?不如将问题表述的更明确:此时此刻的我,是否希望转向定居农业这件事情压根没发生过?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无须一秒钟迟疑,因为若没有定居文明,所有我珍爱与痴迷的一切,艺术,文学,**,历史,哲学,桥牌,图书馆,显微镜,汽车,飞机,计算机,MP3,互联网,维基百科,科学,法律……全都不会存在,连影子都没有。
只有像《人类简史》作者那样的轻浮蠢蛋,才会宣称狩猎采集者也可以拥有同样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也“可能经历过战争与革命,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运动,拥有过深奥的哲学理论,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以及他所统治的半个卢森堡大小的帝国;有着他们自己的天才贝多芬,只是没有交响乐团,唯以竹笛声催人落泪……”
醒醒吧,多数采猎者只有三个数词:one, two, many,能数到5以上已经算了不起,他们的语言缺乏最基本的抽象概念,历史记忆只有两三代,曾祖辈以上的事情便已汇入毫无纵深与细节的神话,仿佛世界一两百年前才被创造,一两百公里之外便只是未知洪荒,道德体系也极为简陋,缺乏自轴心时代以来所涌现的全部道德情感和价值元素,你能指望什么哲学思考?
你果真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世界里吗?那里没有小说戏剧中的动人情节,没有历史长河中的波澜沧桑,战争中的运筹谋略,政治中的合纵连横勾心斗角,竞技场上的欢呼雀跃,曲折迂回的幽默感,面对难题时的苦思冥想,价值默契带来的深切慰籍,胜利与成就的荣耀,以及宗教虔诚,专业执着,侠风义骨,自由精神……所有让你觉得除生存繁衍之外生活还有更多意义的东西,全都没有。
文明确有其暗面,但那遮掩不了其灿烂精彩。
关于“饮食对人类的发展有何意义?”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狼家二萌神]投稿,不代表文本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zwebi.com/cshi/202504-190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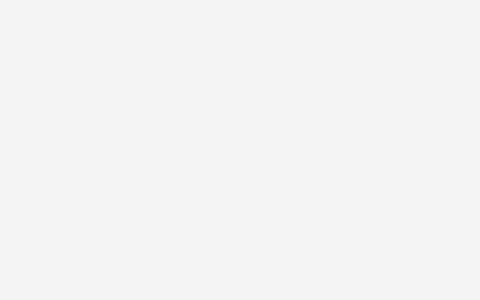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文本号的签约作者“狼家二萌神”!
希望本篇文章《饮食对人类的发展有何意义?》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文本号]内容主要涵盖:国足,欧洲杯,世界杯,篮球,欧冠,亚冠,英超,足球,综合体育
本文概览:网上有关“饮食对人类的发展有何意义?”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饮食对人类的发展有何意义?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